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(第2/8页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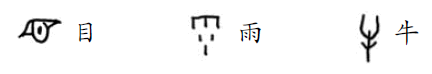
没人知道这个文字体系为何能一直保持稳定。古代中国的口语主要是单音节的(大部分的词都只有一个音节),而且词尾也没有变化(词语的复数、动词时态词尾都不会改变)。有一些语言学家注意到,这些特点让中文天生适用于语标体系。而日语的口语词尾变化就很多,其文字最初只使用中文,但随后就把中文转换成了日语假名表,这个文字体系更为简单,处理词尾变化更加容易。
这个文字体系能保持稳定,有其他学者指向了文化上的因素。中国古代的思想非常保守:祖先崇拜、天生的规律性、抗拒改变、儒家思想理想化过去的方式;这些价值观自然让人们不太可能改变其文字体系。然而这是一个“鸡和鸡蛋”式的理论,且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文字系统为何可以保持稳定。关键是这种文字的稳定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。
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,正式的书写都是用文言。两千多年以前,也就是汉朝的时候,这种语言就标准化了,它只存在于书面语之中。人们用文言写作,但平日说的话却完全不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口语渐渐演变;且整个帝国不断扩张,加入了新的地区和新的方言;但文言却保持不变。明朝的人和汉朝的人说话不一样——他们之间相隔了有十个世纪,但他们都用文言写作。福建人和北京人说的本地话不一样,但如果他们都识字,就能看懂彼此写的东西。文言连接了身处不同时空的人。
如果是字母体系,要维持这种书写的稳定将更为困难。在欧洲,好几个世纪以来,拉丁文都是受教育人士所使用的书面语,然而人们总是有方法把这种书面语转换为本地的文字:字母体系让这种转换对语言本身变得简单。(当然,文化和社会的因素则拖延了转换的过程。)中国也有些白话文,但它很受限制。在语标体系中,白话文较不容易得到发展,不像字母体系,它可以在不同语言和方言中自如地转换。
但中国文字有其他的优点。它为帝国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工具,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它也是各个少数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大混合。文字创造了一种非凡的历史延续感:从无终止的叙述掩盖了过去的混乱。而且中国的文字很美。书法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国艺术,它在中国的重要性比在西方大得多。文字出现在每个地方:在花瓶上,在画作里,或者就贴在门口。每个来访中国的外国人常常都会留意到,文字装饰着像筷子和碗这样的日常用品。在中国的寺庙里,祈祷者传统的做法是写下文字而非说话;算命的人常常靠数名字的笔画来作出预测。19世纪,好些社会组织开始收集写过字的纸片,人们无法忍受把它们当做垃圾随意扔掉。好些地方建起了特别的熔炉,让这些文字能体面地焚化。
当然,书写是很困难的事。中国学生要认字,就要记住几千个字体。由于没有字母顺序,分类变得很困难。(甚至时至今日,到中文文件柜找文件仍然如同一场探险,而且很少中文书会有索引。)第一部中文字典按字形安排文字。渐渐的,很多文字有了第二元素——现在我们叫做“部首”;部首能帮助区别和分类不同的字。但部首本身也是复杂的:第一部中文字典识别了540个部首,还有9千多个汉字。
但在这样一种对文字有强烈认同感的文化中,人们识字的欲望很高。17世纪时,中国已经有了建立完善的商务印书馆,识字的人遍及多个社会阶层,比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范围要广。
来访的外国人记录到,甚至在中国的乡村也能找到书,这是很平常的事;那些书通常是指导手册,教农民如何写简单的合同。依夫林·罗斯基是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,据他估计,18到19世纪,中国男性中识字的比例基本在30%至45%之间,情况和工业化革命之前的日本、英国差不多。罗斯基的结论是,尽管中国未能像这些国家一样快速地工业化,但其差距不能归咎于识字程度。
对于外人来说,中国的文字体系则非常需要进行改革。一个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形容,学习中文就相同于“半殉难”的行动;耶稣会最早为中文制定了使用拉丁字母的系统,这不足为奇了。数百年来,随着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,他们常常会认为把中文字母化会让人们受益。19世纪,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,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劝说人们入教,基督徒就用当地方言出版了圣经。字母化成了传教工作中关键的一步,到19世纪末的时候,外国人和中国的信徒一起,为中国所有主要的方言建立了它们的字母体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