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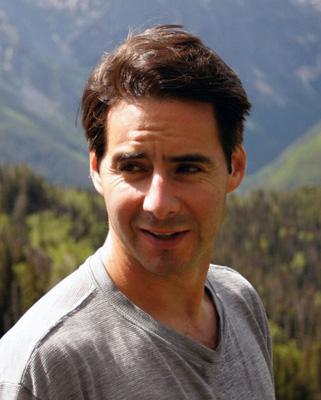
我在四个月内完成《消失中的江城》的初稿。我没有理由写得这么快,没有合约或截稿日期催促着我。我原来可以慢慢来,享受久违的美国生活。但是每一天,我早早动笔,晚晚收笔。记忆驱使我加速写作,因为我担心会失去涪陵生活的实时感。此外,未来也驱策着我:我想记录我对于一个即将面临巨大变化的城市印象。
在过去二十年,这种转变感──经常的、无情的、势不可挡的变化感──一直是界定中国的一个特色。你很难相信,中国曾经给人恰恰相反的印象:根据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里奥帕德.范.兰克(Leopold Von Ranke)的说法,中国是“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”。现在,这是一种最不正确的说法,而作家所面临的一项挑战就是:笔根本跟不上改变的脚步。在《消失中的江城》的第一页,我写道:
涪陵没有铁路,这里向来是四川省一个贫穷的所在,而道路路况十分恶劣。如果你想去哪儿,只能搭船,但是你多半哪儿也不去。
但是,当本书在二○○一年出版时,一条通往重庆的超级高速公路已经完成了,几乎再也没有人搭船沿着长江前往涪陵了,而一条铁路干线正在兴建中。涪陵欣欣向荣,来自终将被三峡大坝淹没的低洼城镇移民刺激它的成长。我以前经常去用餐的小面馆经营者黄家已经开了一间网吧。我教过的学生分散在全国各地:西藏、上海、深圳、温州。但是《消失中的江城》──一部永远停滞不前的书──并没有提到这些。

在一九九九年春天回到中国后,我一年至少去涪陵一趟。由于有了高速公路,现在去涪陵比以往容易多了,而我在北京的作家新生活使我可以自由旅行。我经常去拜访涪陵,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,前往三峡的核心。
在我加入和平工作团的那两年,三峡大坝一直像是一个抽象物──一个模糊的应许、一个遥远的威胁。但是每次我回去,它就变得稍微更加具体。到了二○○二年,移民城已大有进展,地貌明显地划分成过去和未来,在江岸附近,旧的滨江城镇和村庄几乎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。尽管中国其它地方都在一股脑儿地进行兴建,在江水必然会上涨的地方建造任何东西是没有意义的。当局任由这些低洼城镇和村子衰败,直至一切都荒废了:破损的砖、肮脏的瓷砖、布满尘垢的街道。注定毁灭的城镇和新城形成一个对比,新城是由水泥白瓷砖建造而成的,高高座落于河流上方的山丘上。每当我搭船朝长江下游而去,我可以在一系列的水平带状结构中,一眼看出地貌的演变史:江边属于过去的阴暗村落、一段将被水库淹没的绿色农田,以及上面高处一簇簇展望未来的白色建筑物。
我在水坝完成之前的最后一趟旅行,是在二○○二年秋天展开的。我和一位朋友带了帐篷和睡袋,沿着将近一百年前凿在江边峭壁上的古老小径徒步旅行。天气好极了,而小径上的风景令人屏息。有时我们高高位于长江上方,我们所在的峭壁垂直落入三十公尺下的江水之中。每走一段路,我心里就想: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这条小径。
我们朝长江上游前进,而且不急着赶路。在小径走了一星期后,我们参观了正被拆毁的滨江城镇。旧城巫山刚刚被拆除,我漫步于瓦砾中,拾荒者在那儿拣任何可能卖钱的东西:砖和铁丝、草和木头、钉子和窗框。一群人聚集在一堆营火旁边,周围是一栋大型建筑物的破墙,然后,我认出了一块半毁的招牌:他们正在红旗旅馆的大厅扎营,一九九七年我第一次前往长江下游时,曾住在这间旅馆。
所有我最喜欢的滨江城镇都处于各种不同的毁灭阶段。大昌的四分之一已消失了,裴市只留下回忆,大溪已走入历史。有时,我在拾荒者搜刮过后经过一个村子,在寂静中,我审视被留下来的东西。在大溪,我看到一张加了相框的富士山照片,照片的前景是一大片盛开的樱花。在清市,我经过了一张垫料加厚的红椅、一个旧的篮球框,以及一块残破的石碑,上面的刻文是上个世纪完成的。一栋被拆去屋顶和窗的房子仍然有一扇闩上的门。在裴市,我向一对夫妻买矿泉水,他们所住的临时棚子完全是由拣来的门和窗框搭成的。也许这是一个道教的谜语:住在一间由门搭成的房间意味着什么?

当我到达涪陵时,旧城区大部分已被拆毁,新建的住宅区挤在高高的山顶上,城市庞大的堤防差不多已完成了,而乌江对岸的师范专科学校也正在扩张和改变。老干部们已退休了,新干部对外国人比较开放。几年前,我和亚当抵达涪陵时,最先迎接我们的那位友善年轻人艾伯特,现在已是英文系的系主任。当我去他的办公室拜访他时,他拿出我一年前送给学校的精装本《消失中的江城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