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 提高心智,和时间做朋友(第3/13页)
附加工作:给达维陀娃和布里亚赫尔写信,6页——3小时20分钟。
路途往返——30分钟。
休息——剃胡子。读《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》——15分钟。
读《消息报》——10分钟。
读《文学报》——20分钟。
读阿·托尔斯泰的《吸血鬼》,66页——1小时30分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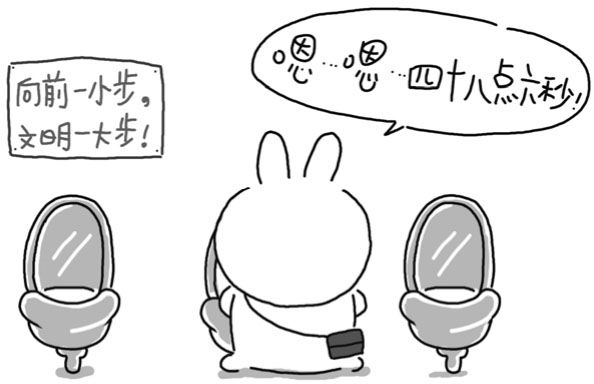
基于过程的记录,不仅更详尽,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好处——遇到结果不好的时候,更容易找到缘由。想明白“基于过程的”与“基于结果的”两种记录之间的区别之后,我开始尝试着在自己记录的每个事件后加上时间。
大约两个星期不到的时间里,我马上体会到了这种新的记录方法的另外一个巨大好处:它会使你对时间的感觉越来越精确。前面我们就讲过每个人都有的感觉“时间越来越快”,以及为什么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。而这样的感觉会使我们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焦虑。焦虑本身没有任何好处,只能带来负面影响。我的体会是,这种基于过程的“事件-时间日志”记录可以调整我对时间的感觉,在估算任何工作量的时候,都更容易确定“真正现实可行的目标”。又恰恰因此总是基本上可以达成目标,于是,基本上可以算是“战胜了焦虑”。
《奇特的一生》我看到第三遍的时候,才真正注意到这段话:
柳比歇夫肯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感。在我们机体深处滴答滴答走着的生物表,在他身上已成为一种感觉兼知觉器官。我做出这样推断的根据是:我同他见过两次面,在他日记中都有记载,时间记得十分准确——“1小时35分钟”、“1小时50分钟”;然而当时他没有看表。我同他一起散步,不慌不忙,我陪着他;他借助于一种内在的注意力,感觉得到时针在表面上移动——对他来说,时间的急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,他仿佛置身于这一急流之中,觉得出来光阴在冷冰冰地流逝。
柳比歇夫这样的人,才是时间的朋友。他们了解时间,通过长时间刻意的训练,甚至不需要表就可以感受时间的一切行动——当然,时间的行动只有一个,自顾自地流逝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在《前言》里写过这样的一段话:
我有个朋友叫做时间。她跟我真可算作两小无猜,默默陪了20多年我才开始真正认识她。她原本没有面孔,却因为我总是用文字为她拍照,而因此可以时常伴我左右。她原本无情,我却可以把她当作朋友,因为她曾经让我明白,后来也总是经常证明,无论做什么事情,只要我付出耐心,她就会陪我甚至帮我等到结果,并从来都将之如实交付与我,从未令我失望。正是因为有了时间作为朋友,我才可能仅仅运用心智就有机会获得解放。
既然“管理时间”是不可能的,那么解决方法就只能是:想尽一切办法真正了解自己,真正了解时间、精确地感知时间;而后再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以及自己的行为与时间“合拍”,就是我的说法——“与时间做朋友”。
最好的工具:纸笔
我把我的“事件-时间日志”称为“时间账本”,里面记录着每天我做过的每件重要事情所耗费的时间开销。而关于它的好处,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必要啰唆。然而,这样貌似简单的记录习惯的养成,远非看起来地那么简单。
事实上,养成任何非天生的习惯,都是需要挣扎才能做成的事情。我们只有一个习惯是天生的——“懒惰”。对每个人来说,懒惰都曾经是天经地义的——谁都得经历或长或短那么一个“衣来伸手饭来张口”的时期才可能长大。在那段时间里,谁都是“随心所欲”的。然而,没有人可以总是“随心所欲”。一度确实可能的“随心所欲”只不过是幼年时的真实、少年时的幻想、成年时的苦恼,老年时的绝望。
西方的宗教里定义了七宗罪,都是所谓的“原罪”——饕餮、贪婪、懒惰、淫欲、傲慢、嫉妒和暴怒。曾屡次出现在《圣经》、著名绘画作品及中世纪教会人士布道的题目中,特别著名。上个世纪末,这些“原罪”也成为电影史上最成功、最具有代表性的心理惊悚片“Se7en”(《七宗罪》)的内容,由大卫·芬奇导演,凯文·史派西、布拉德·皮特、费根·弗里曼主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