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初的呼唤
(以下书信写于1978年李银河去南方开会期间,当时李银河在《光明日报》报社当编辑,王小波在西城区某街道工厂当工人)
你好哇,李银河。你走了以后我每天都感到很闷,就像堂吉诃德一样,每天想念托波索的达辛尼亚。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拿达辛尼亚来打什么比方。我要是开你的玩笑天理不容。我只是说我自己现在好像那一位害了相思病的愁容骑士。你记得塞万提斯是怎么描写那位老先生在黑山里吃苦吧?那你就知道我现在有多么可笑了。
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,就是每三二天就要找你说几句不想对别人说的话。当然还有更多的话没有说出口来,但是只要我把它带到了你面前,我走开时自己就满意了,这些念头就不再折磨我了。这是很难理解的,是吧?把自己都把握不定的想法说给别人是折磨人,可是不说我又非常闷。
我想,我现在应该前进了。将来某一个时候我要来试试创造一点美好的东西。我要把所有的道路全试遍,直到你说“算了吧,王先生,你不成”为止。我自觉很有希望,因为认识了你,我太应该有一点长进了。
我发觉我是一个坏小子,你爸爸说得一点也不错。可是我现在不坏了,我有了良心。我的良心就是你。真的。
你劝我的话我记住了。我将来一定把我的本心拿给你看。为什么是将来呢?啊,将来的我比现在好,这一点我已经有了把握。你不要逼我把我的坏处告诉你。请你原谅了这一点男子汉的虚荣心吧。我会在暗地里把坏处去掉。我要自我完善起来。为了你我要成为完人。
现在杭州天气恐怕不是太宜人。我祝你在“天堂”里愉快。请原谅我的字实在不能写得再好了。
王小波 5月20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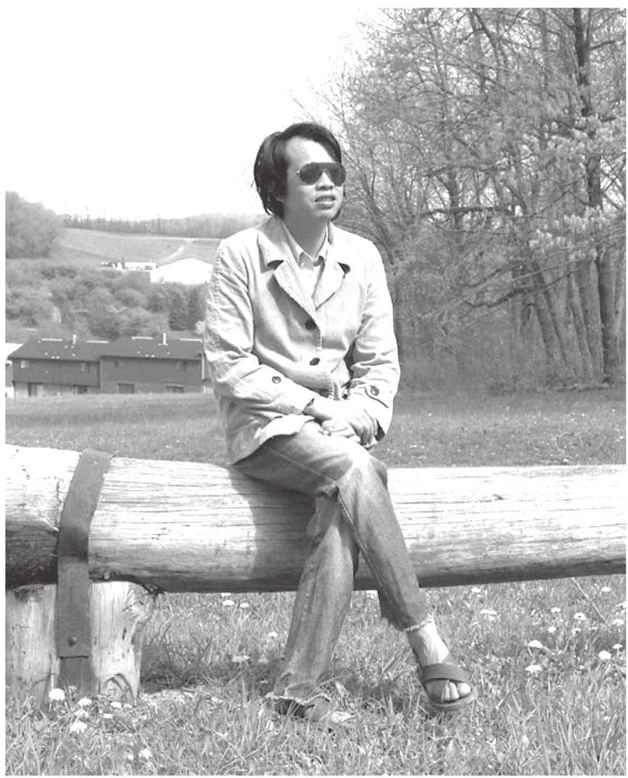
你好哇,李银河。今天我诌了一首歪诗。我把它献给你。这样的歪诗实在拿不出手送人,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
我想念你
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
和你踏着星光走去
想起了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
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
想起了欲语又塞的时候
和你在一起
你是我的战友
因此我想念你
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
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
你是我的军旗
过去和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很麻木。我有点两重人格,冷漠都是表面上的,嬉皮也是表面上的。承认了这个非常不好意思。内里呢,很幼稚和傻气。啊哈,我想起来你从来也不把你写的诗拿给我看。你也有双重人格呢。萧伯纳的剧本《匹克梅梁》里有一段精彩的对话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:
息金斯:杜特立尔,你是坏蛋还是傻瓜?
杜特立尔:两样都有点,老爷。但凡人都是两样有一点。
当然你是两样一点也没有。我承认我两样都有一点:除去坏蛋,就成了有一点善良的傻瓜;除去傻瓜,就成了愤世嫉俗、嘴皮子伤人的坏蛋。对你我当傻瓜好了。祝你这一天过得顺利。
王小波 21日
你好哇李银河。今天又写信给你。我一点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,所以就不能谈论你的工作。那么怎么办呢?还是来谈论我自己。这太乏味了。我自觉有点厚颜,一点也听不见你的回答,坐在这里唠叨。
今天我想,我应该爱别人,不然我就毁了。家兄告诉我,说我写的东西里,每一个人都长了一双魔鬼的眼睛。就像《肖像》里形容那一位画家给教堂画的画的评语一样的无情。我想了想,事情恐怕就是这样。我呀,坚信每一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该是眼前的世界。眼前的世界无非是些吃喝拉撒睡,难道这就够了吗?还有,我看见有人在制造一些污辱人们智慧的粗糙东西就愤怒,看见人们在鼓吹动物性的狂欢就要发狂。……我总以为,有过雨果的博爱,萧伯纳的智慧,罗曼·罗兰又把什么是美说得那么清楚,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再是愚昧的了。肉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赞美了。人们没有一点深沉的智慧无论如何也不成了。你相信吗?什么样的灵魂就要什么样的养料。……没有像样的精神生活就没有一代英俊的新人。
出于这种信念,我非常憎恨那些浅薄的人和自甘堕落的人,他们要把世界弄到只适合他们生存。因此我“愤懑”,看不起他们,却不想这样却毒害了自己,因为人不能总为自己活着啊。我应该爱他们。人们不懂应当友爱,爱正义,爱真正美的生活,他们就是畸形的人,也不会有太崇高的智慧,我们的国家也就不会太兴盛,连一个渺小的我也在劫难逃要去做生活的奴隶。如果我不爱他们,不为他们变得美好做一点事情的话。这就是我的忏悔。你宽恕我吗我的牧师?